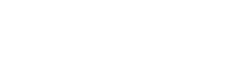胡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案
案情简介
在李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一案中<长寿“砂霸”案>,胡某某被指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共犯>、串通投标罪<共犯>,现该案已经一审判决。
对于本案二审,辩护律师重点阐述了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上是由“以李某为交叉点的两个不同群体”、不能混为一体;同时,对共同犯罪的刑法理论等内容进行了深入阐述。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受胡某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胡某某二审的辩护律师,现辩护人按以下四部分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关于胡某某是否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
第二部分关于胡某某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一案;
第三部分关于胡某某是否构成串通投标罪一案;
第四部分本案是否适用牵连犯-从一重罪之规定的问题。
对于上述内容,现辩护律师分别加以阐述:
第一部分 关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
一审判决认定:2004年以来,李某勾结胡某某、郭某、项某某,又纠集吴某、王某等人,多次实施聚众斗殴、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打击报复证人、非法买卖松动、弹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暴力性违法犯罪活动,结成了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逐步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辩护人认为,从结合源头而言,不是勾结,而是合伙;从主观明知而言,不具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要件;从全案事件的分类而言,是分别来自于以李某为交叉点的两个不同群体之内的事件。
一、从结合源头而言,不是勾结,而是合伙。
一审法院认定从2004年以来,李某勾结胡某某、郭某、项某某;对此,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妄下定论。
1、首先需要解释的什么是“勾结”,根据百度词典和现代汉语词的注解,其基本解释是“暗中作不正当的联系、结合”。
2、从李某与胡某某等三人的结合而言,是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民事合伙关系,属于民事合伙组织,并非为不正当之事而结合在一起,从以下笔录摘要可以还原当时的背景:
李某
海损事故后,海事处通知长寿段的采砂业主开安全会,会后我找到项某某,我跟他说他没有采砂证,我有采砂证,让他给我一起做采砂生意,他用我的采砂证和采砂船,他出运沙船和码头,生产经营等具体管理由项某某管理;我与项某某谈合伙经营河沙的时候,发现项某某、郭某、胡某某是一伙的,我和项某某谈好后,其实相当于与项某某、郭某、胡某某三个人谈好了合伙采砂的事情。
项某某
长寿12.18海损事故之后(注:事发于2002年),长寿海事处召集船主开会,要求我们必须要有证才能继续采砂,我和胡某某、郭某的采砂证只能采岸砂,只有李某的许可证能采河砂,但李某只有采砂船,没有运砂船,李某找到我说让我跟他合作,经过几次商量,我们开始合作;后来,我又把胡某某、郭某也拉起来合作采砂。
郭某
长寿河道管理处说采砂要办证,并且说我们的坐标为被李某办理了,我们办不了,于是,我们只有偷偷的采,后来,水务局海事执法大队就召集我们开会说,只有李某有许可证,可以采砂外,其他没有证件的,任何人都不能采砂。
胡某某
由于我、项某某、郭某不能采砂,所以,我们就到长寿农机水利避讨说法,但农机水利局说采砂证已被李某办了,不能再办证了。
以上供述很清楚的反映了李某与胡某某等三人是各取所需、互为所用而结成的民事合伙经营组织,并非是为了不正当之事而结成非法同盟,而且,该合伙组织具有排他性,排除四人之外的所有人;事实上胡某某、项某某、郭某也正是基于这一宗旨而延续与李某的合作,即便是在本案中所涉嫌的犯罪行为,也是与该宗旨紧密相关的。
综合以上两点不难看出,一审法院将“合伙经营”认定为“勾结行为”,属于黑白颠倒、刻意而为之,具有主观定罪的嫌疑。
二、从主观明知而言,不具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要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主观明知问题,并不要求其主观上认为自己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即可认定。 具体到本案,胡某某等三人与李某的合伙经营组织虽然存在违法犯罪活动(按一审认定),但并非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组织,从2004年至今共7年,胡某某、项某某、郭某共涉嫌寻衅滋事、行贿、串通投标,很显然,该合伙组织并非是以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内容.
至于合伙组织中的成员李某是否单独、或参与其他群体实施违法犯罪,辩护人认为这与胡某某乃至项某某、郭某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胡某某等三人也无权干涉李某的个人行为.
三、从全案事件的分类而言,是分别来自于以李某为交叉点的两个不同群体之内的事件。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而言,除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外,其余涉罪案件并非都是来自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群体,即以李某为群体成员之一的松散群体(即:李某、吴某、王某、李某、李某锦、李某、向某等人)和以李某为合伙人之一的紧密群体(却:李某、项某某、郭某、胡某某四人组成的合伙经营组织),虽然这两者都与李某有关联,但并不能因此把这两者结合为一体、构成一个统一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1从辩护人所分类的两个群体的人员关联性而言,除李某外,两个群体之间的其他人员几乎互不联系,甚至互不认识,完全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不符合一个统一体的人员结构.
2从辩护人所分类的松散群体中行为人的行为特征而言,该些成员所涉犯罪的类别多\数量多\人员多\暴力胁迫多;
而从辩护人所分类的紧密群体中行为人的行为特征而言,行为人所犯罪的类别单一\数量仅为三件\人员总四人(包括李某)\除仅一起寻衅滋事外,没有任何暴力胁迫犯罪,特别显著的是该些行为的基础事实均是来自经营活动,并非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要求的“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综上,李某与胡某某等三人所形成的群体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是合伙组织;胡某某也不属于以李某为群体成员之一的松散群体中的成员;更为关键的是、不能把两个不同的群体因为李某的存在而进行串联、并混同为一个统一的组织。
第二部分 关于寻衅滋事一案
一审判决认定:胡某某、项某某、郭某的供述均证实,其与李某合伙经营河砂期间,由李某负责解决经营过程中的各种纠纷。胡某某等三人对于河砂涨价后所引起的纠纷由李某安排人员解决具有共同的故意,且事后对于李某从四人的共同经营款中拿钱赔偿给对方也予以认可,故胡某某、项某某、郭某已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共犯,其提出未与李某共谋邀约吴某殴打他人的辩解虽属实,但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
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将本起案件认定为共同犯罪,属于定性错误。
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逻辑思路
1关于共同的犯罪故意:
胡某某等四人在合伙经营期间,由李某负责解决经营过程中的各种纠纷;这表明了两点:第一、胡某某等人具有由李某“解决纠纷”的共同故意;第二、胡某某等人对李某的“解决方式”持有“概括故意”,可能包括以“犯罪方式”进行解决。
2关于逻辑印证问题:
因河砂涨价而引发的犯罪事件(按一审认定)之后,李某从其四人的经营款中拿钱赔偿,胡某某等三人均予以认可,由此分别印证四人具有由李某“解决纠纷”的共同故意、也具有对李某的“解决方式”包括以“犯罪方式”进行解决的概括故意,由此推断:四人在事前有概括的犯罪故意,事后胡某某等三人认同和接受犯罪事实并进行赔偿,所以,四人属于共同犯罪。
二、关于辩护人的观点
1关于胡某某等人对李某“解决纠纷”的“解决方式”是否包含以“犯罪方式”进行解决的问题。
辩护人认为,在胡某某等三人的故意范畴中不包含李某以“犯罪方式”进行解决,而仅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化解,而且,在本案中,无论是李某的供述、或是胡某某等三人的供述,均无法证实在胡某某等三人的故意范畴中已表达了李某可以以“犯罪方式”解决纠纷;而且,在本案发生之前,也没有可类比的刑事案件发生;所以,从证据、事实而言,无法证明胡某某等三人的共同故意中已包含犯罪故意。
2退一步讲,即便在胡某某等三人的共同故意中,对李某“解决纠纷”的“解决方式”中包含以“犯罪方式”解决纠纷,那么,这是否属于刑法中“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辩护人持否定的观点。
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对共谋计划应当是具体的、并具有针对性的;如果共谋计划是笼统的、不确定的概括的故意,并未明确约定犯罪时间、地点、对象、手段等内容,则共谋而未实行者就不需要对该次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在该次行为中共谋而未实行者与其他共行者不构成共同犯罪。
结合本案,即便在胡某某等三人的共同故意中、对李某“解决纠纷”的“解决方式”包含以“犯罪方式”解决纠纷的故意,但这种故意显然是笼统的、不确定的,不指向任何特定的事件,因此,不能成为共同犯罪中的共同故意。
3关于事后赔偿的问题,能否印证胡某某等三人在事发前就已经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或者能否追认自己就是“寻衅滋事”的一员?
第一、一审法院以事后赔偿去印证事前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这显然属于逻辑错误。事实上,事后赔偿与事前是否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之间没有任何对应关系。
如果事前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事后并非一定得去赔偿,现实中没有进行赔偿的现象占绝大多数;如果事后给予赔偿,也并非完全是因为事前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也可能仅仅具有民事授权的意思表示。
第二、在民事范畴中,事后追认可能导致对该起民事案件承担民事责任的后果,但在刑事范畴中,事后赔偿并不能导致追认自己对刑事案件承担刑事责任的后果,这有别于民事追认的效力。
4关于胡某某等三人是否实际参与寻衅滋事一案
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内容可知,胡某某、项某某、郭某并未与李某共谋邀约吴某殴打他人,根据我国刑法学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共同犯罪理论,除必须有共同故意外,还必须有共同行为。所以,即便胡某某等三人与李某存在共同故意,但并不存在共同行为,也理所当然的不构成共同犯罪。
综上,一审法院对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存在认知不够、理解不准,在本案中,又因逻辑推理错误,导致最后定性错误,因此,辩护人认为胡某某、项某某、郭某均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共犯。
第三部分 关于串通投标一案
一审判决认定:郭某、项某某、与李某共谋串通投标,参加投标并协助李某取得了采砂许可证,在其后的经营过程中利润平分,二被告人在串通投标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胡某某参与共谋串通投标,并提供了20万元投标保证金的事实,有四被告人的供述予以证实,胡某某已构成串通投标罪的共犯。
对于一审法院的认定,辩护人持否定观点。辩护人从胡某某是否参与了“共谋”和胡某某是否参与了“共行”两个阶段来阐述:
一、关于胡某某是否参与了“共谋”的问题
在本案证据中,很清楚的反映了共谋的所有过程:首先是李某与水利局局长程德华进行共谋,暗定李某中标、招标方式采用“邀标”、由李某提供围标人、泄露标底20万;然后,李某将与程德华的共谋内容告诉了项某某、郭某,并商议由项某某、郭某、李某三人投标、确定报价。辩护人认为,这就属于本案真正意义上的“共谋”。
至于有谁告诉了胡某某什么内容,并不属于胡某某参与共谋的结果;而且,在本案的所有证据中,均未体现出李某、或项某某、或郭某告诉了胡某某--他们是如何与程德华共谋的?他们是如何串通投标的?只告诉了胡某某他们三人要支投标。因此,辩护人认为,胡某某不仅未参与“共谋”,也并不知晓李、项、郭之间“共谋”的具体内容,更不能因为胡某某“知道”(另外三人要去投标)而“犯罪”。
二、关于胡某某是否参与了“共行”的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不仅需要“共谋”,还需要“共行”。就本起事件而言,虽然胡某某有所行为,但并不是在胡某某参与“共谋”之下的“行为”,而是在他人共谋之下、受他人安排而所实施的行为,与李某等三人的共谋行为、不能结合成刑法意义上的共同行为,因为他不在共同意志之下。
第四部分 关于牵连犯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定李某等四人同时构成行贿罪、串通投标罪;辩护人认为,在串通投标罪一案中,存在与行贿罪相牵连,属于牵连犯,应以行贿罪论处。
李某等人为了获得采砂权,与程德华商议采用邀标方式进行招标,并由李某确定投标人进行围标,事后,李某为表示感谢而向程德华等人送去感谢费数十万元。一审法院亦将该金额计入李某等人的行贿金额之中。
辩护人认为,在本起事件中,李某是以不法获得采砂权为目的,为此,实施了串通投标和向程德华等人行贿的行为,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并分别触犯了串通投标罪和行贿罪,这些内容完全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因此,辩护人认为,本起事件具有典型的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根据刑法理论,应从一重罪论,即:行贿罪,而不应同时追究串通投标罪。
综上所述,在本案中,胡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和串通投标罪。望贵院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职能,依法裁决。
上一篇:谭某某被控巨额持枪抢劫罪案
下一篇:震惊海内外的希尔顿酒店涉黑案